大学时期,选择读研是因为觉得自己还没有做好工作的准备,想着读研应该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,每天在实验室里做实验、摆弄各种瓶瓶罐罐、跟形形色色的物质打交道。懵懵懂懂的博士生涯中,只想着做好实验,顺利毕业,从未思考过科研在我们成长中的作用。
回到师大,房老师经常在组会的时候跟我们说:“科研是锻炼人、培养人最好的途径”。起初,我并不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含义。直到看着一届届师弟师妹,经过严谨的科研训练,逐渐从一个个小孩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小伙子、大姑娘,我才慢慢开始理解这句话。同时,我也不禁会去反思自己在科研中的成长,是否也像他们一样实现了蜕变?细想在组里学习的这些年,我的确学到了很多,也正是这些收获与成长给了我鼓舞,让我有了继续学习的动力。
我访学所在的学校是英国南安普顿大学,合作导师是Steve Goldup教授,研究方向是机械互锁分子(Mechanically interlocked molecule)。机械互锁分子属于目前化学领域非常前沿的研究内容,该类分子的合成也极具挑战。无论从研究课题的相关性,还是实验技能的需要方面来看,我都不具备胜任这个课题的能力。因此,我又非常开心的成了一名“研究生”,在导师的指导下和实验室的伙伴们一起学习、做实验,架反应、过柱子的生活每天都非常充实。

细心观察就会发现,优秀的人其实都很像。在师大,房老师是我们的榜样,特别佩服房老师永远都是那么的精力充沛。在南安普顿大学,Steve也是一样,雷打不动的早七点到晚六点,见面的“How are you?”之后肯定是“How's chemistry?”虽然午饭只有一个简单的三明治,但是他每次都会约一个人边讨论实验边吃。Steve似乎不像大多数人眼里的英国教授,因为他真的太“卷”了。这也勾起了我对“卷”这个词的重新思考,也许“卷”更多的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评价当事人的行为,原本当事人的愉悦和享受,在旁观者眼中就变成了痛苦和煎熬的“卷”。我在想,这也许是就是成功者都散发着乐观向上正能量的原因吧!
新的实验环境里,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,周围的人都成了我的老师。尤其是热心肠的Andrea,一个来自意大利的三年级博士生。虽然口头禅是“I am a loser”,但是Andrea几乎每天都是第一个到实验室并最后一个离开的人,他也是实验室里知识最扎实的研究生。所以,我觉得用“说最消极的话,做最积极的事”来形容他,最合适不过了。印象特别深刻的是2023年元月底的一天,早上刚到实验室,Andrea就特别沮丧地过来跟我倾诉,说他做了一年的一个课题dead了,当时气氛瞬间凝固。我试图绞尽脑汁地去想怎么安慰他,但始终想不到合适的语言,因为我很清楚,他的前驱体合成需要经历20多个反应步骤,这个打击对他来说太大了。沉默片刻之后,Andrea跟我说,他需要尽快找导师讨论。从导师办公室出来之后,我特意去找他了解情况,他说老师跟他一起分析了结果,然后说了一句“Fine, we are learning”。下午,Andrea又开始了自己忙碌的实验…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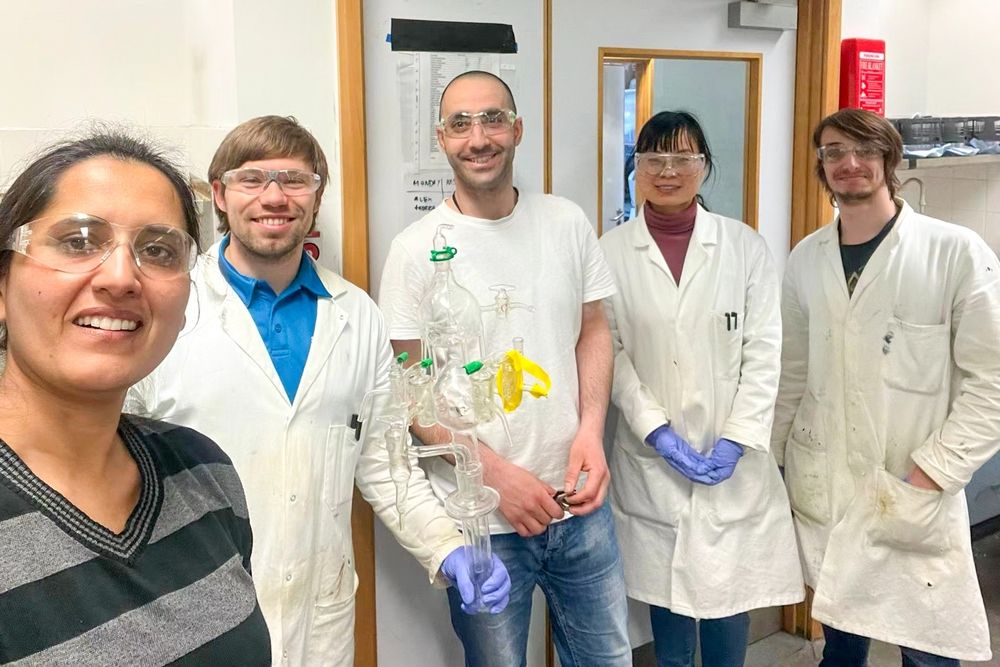
访学期间实验室的小伙伴们,从左到右分别是Mandeep博士后,Martin博士后,Abed博士后,我,Andrea博士生。
仔细想想,其实也正常,因为失败本来就是科研的常态,任何一项伟大的成果都是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之后的结晶。我们都知道“失败是成功之母”,也都听过伟人们面对一次次失败,坚持不懈,最终成功的故事。但是,当真正面对失败的时候,我们却很难做到不气馁、不放弃,因为这需要很强的意志力。我想,Andrea课题的失败,也只是课题组遇到的众多失败中的一个,与其花精力郁闷、颓废,还不如重新整理思路、换一种方法继续做事情。这件事情,也让我体会到团队“铁人精神、阿Q精神、办法总比困难多”科研文化的另一层含义,但问耕耘,莫问收获,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,不要太在意结果,更不要因为不好的结果而影响前进的步伐。
虽然相距8000多公里、研究方向迥然不同,但是两个团队其实很像,都有“Live for Science”的leader、勤奋的学生和积极向上的科研氛围。在南安普顿大学化学学院,每次有人问我从哪里来、做什么研究方向的时候,我都会立刻打开团队的网站,给他们一一介绍。尤其是有一次,楼上一位做荧光的波兰博士后告诉我,他读过房老师的文章,还跟周围人说我们团队在传感方面做出了很多出色的工作,那个时候真的无比开心。
很庆幸自己遇到了这么多好的老师和实验伙伴,能有机会在科研的道路上学习、成长。读不完的文献,做不完的实验,解决不完的问题,都将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!